看更多編輯精選文章

吳學儒/從「手榴彈事件」出發:漢人社工如何在原民部落學習、進退、培養文化敏銳度?

張雅晴/走進國際性別現場:從紐約 NGO CSW 論壇,看不同國界的性別平權挑戰

東亞與歐洲照顧年會:打造社區照顧生活圈、正視長照成本上升與人力不足、保障移工

6個提問認識「微笑憂鬱症」:和憂鬱症有什麼不同?看起來很快樂,但內心很憂鬱?/《微笑憂鬱》

「以兒少為中心」的兒童節目如何製作?孩子的各種樣貌與悲喜,都值得被看見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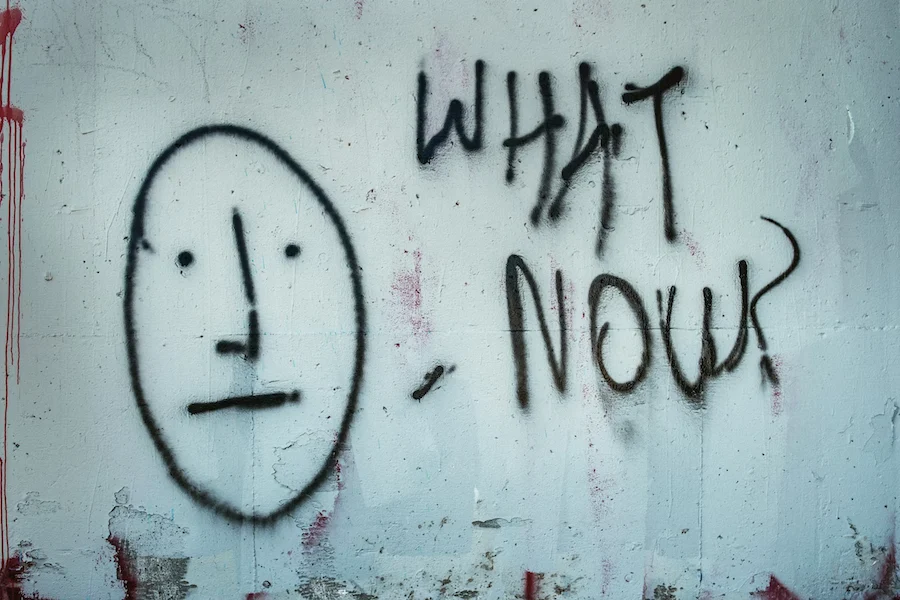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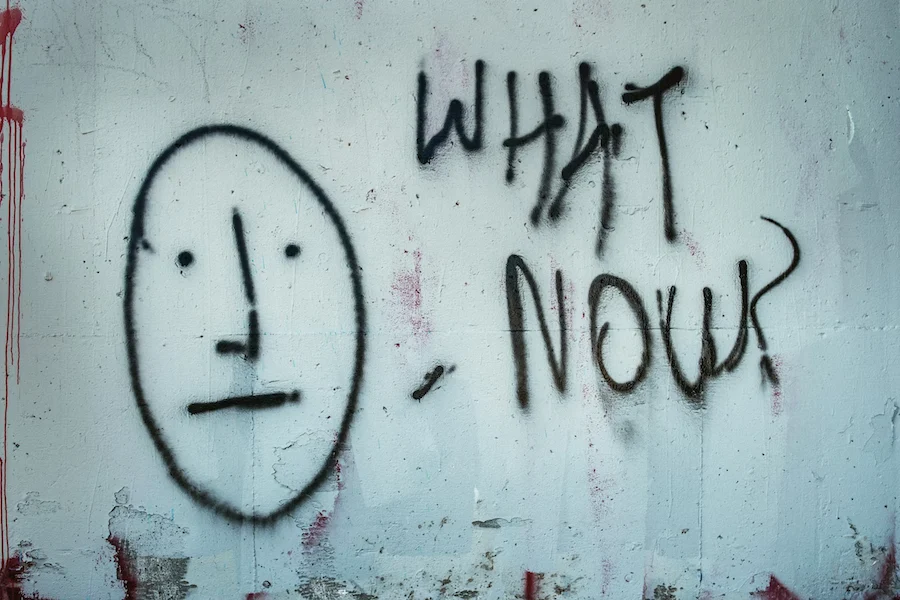


《結案》2014.8.4 by 郭可盼
我是不是應該
把我的靈魂撕開
撕成一片一片小小的
好讓你隨時帶著
把最好的我帶著
讓你在痛苦而猙獰的時刻
讓你在無助而徬徨的時刻
讓你將人吞吃入腹卻又將自己乾嘔出來的時刻
有凝視的眼光坐臥在你的影子之上
並不擁抱你 只是
一遍一遍輕輕日曬著你的青春
直到眼淚過去
直到喧嘩消聲
這樣你就不用一覺醒來
在冰天雪地的床鋪上痛哭失聲
而我也不需要教導你離別
因為我從來也學不會離別
我從第一份做青少年服務的社工工作離職後,出國去念研究所。在研究所的假期間回臺灣時,曾在和前單位討論過後,和一個結案已久的案主約吃飯。
我們閒聊著一些日常生活的話題,接著素來驕傲的孩子沉默了一會,說:「當你離開的時刻,我覺得自己的世界都快毀滅了。」
當我們分開後,我寫下了上面這首詩。
那時候我心都碎了。想著專業關係到底算什麼?你努力和一顆破碎的心建立關係,然後在他信任你的某一天,告訴他關係要結束了。不管設計再多結案的鋪排過程讓對方準備,這仍然是很違反人性的事。
那個和你一起面對生活各種困難的人、一起在各種新的嘗試中討論、一起煩惱的人,忽然有一天就從你的日常中脫離了。這樣的意義到底是什麼?這段關係滿足的到底是誰?
有好長好長的時間,我反覆想著這個問題,不知道怎麼去面對那些對我交付珍貴信任的少年。他們明明那麼傷心,甚至不願意責怪你。

社福組織在申請方案時,必須和經費補助單位(像是政府)協調服務的對象、時間與結案標準。有些服務有明確的時間(例如學生畢業)、也有些是議題緩解(例如自殺意念減緩),或是能銜接到別的資源。
對於一個一線社工而言,社工通常被方案決定工作的長度,但方案在設計的過程中,鮮少詢問一線工作者與服務對象的需要,往往是在各種行政安排的妥協中自行決定了服務次數與時間,有時候因為要達到方案要求的案量,還必須結掉部分個案才有開新案的空間。
而結案與否更常並不掌握在案主手裡(可能就像很多時候,開案與否也掌握不在他們手裡),服務能不能繼續也往往不是他們說了算。後來我遇到許多案主,他們到後來也習慣了社工的來來去去,變成聊聊天說些困難可以,但也不需要多較真,看看有什麼資源可以使用這樣就好。畢竟那些生命的艱難,也不必過度期待眼前的工作者能陪你走得多久或多深刻。
關係的分別固然都讓人傷心,但社工的服務型態也讓結案變得很艱難。
那個一天到晚來你家拜訪,你全家都認識、大家有什麼困難都等著他來討論的那個人,好像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,成為一家人重要的夥伴。特別是比較脆弱、外部資源比較少、風險高的家庭,當部分任務完成,這樣的關係要抽走時,家庭中其實都還有很多困難和不安。
再加上,社工的案量真的太滿了,即便案家現在穩定下來了,之後再遇到風險或挑戰時,也可能會排不到社工的服務,因此對家庭來說,結案也常常是很恐慌的事。

沒有在適合的準備下、在適合的時機裡、用適合的方式好好的說再見,有時候對於一些過去受過傷的人而言,是遺棄的再現。對於有些人來說,這個歷程讓他對未來再接受其他的服務充滿了疑惑和抗拒。對於有些人來說,他的生命來了很多人重複問著類似的問題,但在很短的時間內、好像沒有幫到什麼忙的時刻,這些人又都走了。
要討論如何好好結案,絕對沒有辦法只討論個別社工應當如何做,可能更要去思考體制現下的困境。就像一般醫療衛教文章常會教導病人不要症狀改善就停藥,而是需要把療程走完,例如抗結核的藥物需服藥 9 個月以上才能根治、避免復發。
那麼,為什麼我們很少探討和檢討,一線工作者服務特定議題的案主,到底合適的服務長度是多久?沒有按照需要的品質、頻率、長度提供所需的服務,很可能怎麼結案都會是錯的。
例如,自殺關懷訪視員(自關員)的關懷訪視服務期程為 3 個月,可延續至 6 個月,如果再延長就必須特別經衛生局同意。通常一個人結束生命時,往往是生命中各種內在、外在層層疊疊的困境交織到再也無法承擔的時刻,然而在自關員高案量(聽過一人有到 200-300 案)和極短的服務時間下,可能只能提供資源的連結和電訪關懷。
很多案主因此受困於結案、出事、開案的循環中,也有些案主和自關員彼此敷衍,說一些我很好我沒事的話,避免自己被反覆「關懷」。
對公部門而言,服務的覆蓋率可能是第一優先被考量的事,也是行政單位被審計單位、立法院檢視時最容易證明成效的方式。對於申請方案的社福單位來說,心裡更常有小警總,覺得方案的服務量要衝高,不然補助可能下不來,而且這些數字只能一年比一年高,沒有什麼調降的空間。

衝高的服務量必然稀釋服務的品質,或必須趕快結案以收新案,例如社區關懷訪視員(社關員)在很多縣市,一個人一年要服務 80 案以上的社區精神病人。因為案量太高,很可能必須把部分案主結案,否則手上同時掌握的案量會超過負荷。
討論結案之前,還是要先有好的服務啊。如今各種既定的服務,其實都很需要一線工作者和服務使用者回頭檢視、討論和修訂。
另外一個體制的困境是,很多工作者雖然會服務案主到穩定的狀態後結案,但是結案後,因為案主沒有人可以討論困難、能力也不足以應付生活中的挑戰,或是失去與社會的連結,反而無法繼續穩定生活,產生風險。
一個社工不結案或無法結案,常會被指責是工作沒有成效,但這可能忽略了,有些人的確可以藉由一段服務過程,逐漸長出面對生活、和身邊的人建立關係的能力,社工便可以逐漸淡出他的生活。但也有些人,他個人的狀態和他的家庭能量,可能需要有人長期在旁邊協助和支持,以免他陷入孤立。
社工如同輪椅,像是「輔具」一般的存在。在這樣的狀況裡,其實需要的也不是結案,而是提供「不結案」的服務方式。
雖然提到很多體制的困境,但我個人也有很多經歷和學習。在第一份工作結束後,一些服務對象對於結案的受傷,讓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反省自己,是服務的過程中出了哪些問題,讓結案後對方反而墜落了。

一開始當社工時,會著重於和案主建立深刻的關係。我覺得如果這段關係滋養了對方,那對方就可以有力量去面對生活中的挑戰。但很多時刻我也過於天真,對於案主而言,面對挑戰需要的不只是單打獨鬥,也很需要身邊的人在生活不同層面的支持。
沒有協助案主建立足夠強韌的支持系統、沒有修復和推動個案家庭比較好的溝通方式,當社工結案了,案主好像也就陷入了孤立無援的狀態。
所以此刻的我,可能會更把重點放在「案主如何和身邊重要的人建立關係」。像是常常被極端情緒困擾的精神疾病當事人,過往我可能著重在我如何接住他的情緒,但現在可能花更多力氣在如何讓他身邊的人知道怎麼接住他、如何讓願意幫忙的人建構安全的支持網絡,避免讓單一的主要照顧者累壞了。
雖然這篇文章的標題在談結案,但其實說到此刻,談的都是服務。若我們真的能依照需要給出適合的服務、給予足夠的時間陪伴案主度過生命中的危機、協助他們建構穩定的支持網絡,才是真的能夠「好好說再見」的基礎。
面對關係的結束,心情複雜的不只是服務對象,也有一路同經風雨的工作者。結案逼著我們回頭檢視同行的旅程,有時候對自己說「不要為自己的失責找開脫」,有時候又會說「即便對方生命仍然辛苦,但我們的同行並非毫無意義」,持續在 2 個不同的觀點間掙扎。
其實我也是很討厭說再見的人,討厭各式各樣的分別,覺得分離就是各種沒辦法、各種無可奈何和不得不,只有傷害大小的分別。

在英國念戲劇治療時,我們需要在實習中提供一定時數的戲劇治療。隨著學期結束,我和案主也到了工作的尾聲。面對結束,那時刻的我被打敗了。過去結案時,那些對方的傷心洶湧而上,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,也不知道該怎麼賦予這樣的關係意義── 除了我拿到了學分,我到底提供了對方什麼?
和我工作的對象是一個學習遲緩、沒有語言能力的孩子,在倒數最後的幾堂課時,他開始發展新的遊戲方式。在新的遊戲方式裡,他不需要你時時陪他玩,而是看看你,知道你還在,就可以自己去探索新的空間和玩具。
那時候,我忽然覺得這個不會說話的孩子,教了我一堂很重要的課,讓我學到一種對於「說再見」新的看法。
那些我們服務的對象,曾經在一段艱難的時間裡和我們非常親近,但是慢慢的,有一天他們有足夠的能力可以面對生命了,像是成年的孩子背起行囊離開父母,開始下一段旅程。
離別難免有傷心,也難免有眼淚,但很多時候,離別也可以視為一種歡慶,歡慶我們共同的旅程到了一個段落,對方要往新的篇章走去了。雖然以後的旅程不會繼續同行,但是我們在彼此身上學習了一些很重要的事,生命也因此豐厚。這真是令人傷心的事,但同時也是一種歡慶呀。
希望在職涯中,每一個工作者都也能被溫柔以待,回想起這些和服務對象的旅程時,不只有疲憊和傷感,也可以感受到彼此生命豐厚的歡慶。
延伸閱讀:
1. 郭可盼/如何成為關係的轉譯者,ㄧ起邁向「好好生活」?
2. 郭可盼/我可以和服務對象成為朋友嗎?社工與案主,那條無形浮動的界線
3. 郭可盼/對不起,我沒辦法善待你,因為我太久沒有善待自己
4. Right Plus 專欄【一種__的社工觀點】